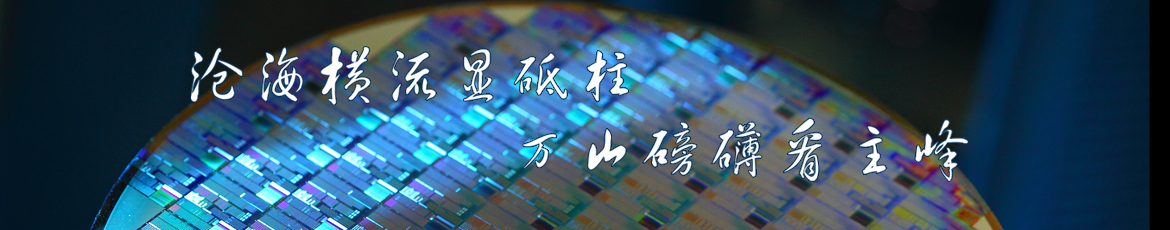

1987年2月20日凌晨,制备出起始转变温度92.8k的钇钡铜氧超导样品后,物理所13位研究者的合影。物理所供图
1987年2月20日凌晨,一张合照在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以下简称物理所)诞生。照片里的13位研究者眉头舒展,他们刚刚书写了中国超导研究的新历史:制备出起始转变温度92.8开尔文(K,约合-173.15摄氏度)的钇钡铜氧超导样品。
合影中,46岁的赵忠贤坐在第一排最右侧,1989年,他作为第一完成人,与研究集体共获国家自然科学奖一等奖。这是中国学者在超导领域首次取得重大突破,由此掀起了全球的高温超导热。
之后20余年,热度渐散,有人转行、离开,而以赵忠贤为代表的一批人仍在默默坚守。
2013年,连续空缺3年的国家自然科学奖一等奖花落物理所和中国科学技术大学(以下简称中国科大)。赵忠贤又一次作为第一完成人,与中国科大教授陈仙辉等人凭借在铁基高温超导领域的卓越贡献获奖。
高温超导自出现以来,不断颠覆人们的固有认知,旧理论已无法解释新现象。恰恰在这无理可循的几十年,中国学者抓住机会,将板凳坐热,掀起又一轮高潮。
扎根:判断力+勇气
超导是指某些材料在降到一定温度时,电阻消失为零的现象。既有重大的应用前景,又是迷人的科学问题。
1986年,瑞士科学家贝德诺兹和缪勒首次在镧钡铜氧化合物中观测到超导电性,临界温度高达35K——在此之前,人们普遍认为超导体一定来自常规金属和合金,且临界温度不会超过40K,即存在“麦克米兰极限”。而缪勒等人用到的材料是金属氧化物。“此类材料多半是绝缘体,这与超导似乎格格不入。”2013年国家自然科学奖一等奖共同完成人、南京大学物理学院教授闻海虎告诉《中国科学报》。
这一发现引起了赵忠贤的共鸣。其实早在上世纪70年代,他就曾大胆设想:更复杂的结构材料可能催生出更高临界温度的超导体。
看罢论文,赵忠贤立刻找来自己在中国科大的同学陈立泉、黄玉珍夫妇,几个人分头做测试和样品制备。1986年12月,陈立泉在黄玉珍合成的样品中观察到临界温度70K的超导现象,但实验结果没能重复。这期间,美国、日本的学者相继发现了更高临界温度的新型超导体,研究小组顿时压力倍增。
1987年春节,赵忠贤和同事坚持工作,从原材料、实验方案、制备方法等方面找原因,最终发现样品的氧含量差异是决定超导与否的关键。历经数十个小时不眠不休,他们终于迎来了文章开头那一幕。当天凌晨,赵忠贤等人合影完又接着制备样品,直到测出三批样品全部超导,且临界温度都在液氮温区,才松了口气。
“瑞士的两位科学家是打开窗户的人,我们进去以后,把它做到液氮温区。”赵忠贤回忆。受制于转变温度,以往超导研究不得不使用昂贵的液氦,更低成本的液氮让后人看到了更多曙光。
1987年2月24日,中国科学院数理学部召开发布会,正式公布赵忠贤等人制备超导样品的元素组成:钇钡铜氧。次日,他们的成果登上《人民日报》。
同年3月,美国物理学会年会临时增加高温超导专门会议,千余人的会议室挤得满满当当,赵忠贤作为最重磅的发言人之一,作了整整20分钟报告。会议从晚上7点多一直持续到第二天凌晨。
高温超导研究迎来世界范围的热潮。尽管当时中国的研究条件比国外差得多,但仍作出关键贡献。
“赵老师他们敢于在氧化物中寻找新型超导体,说明有独特和敏锐的判断力,也需要勇气。”闻海虎说,“我想这就是从0到1的发现。”
积累:兴趣很重要
1987年前后,国内超导研究热度达到顶峰。“只要你有炉子,很容易就烧出样品来。”超导国家重点实验室主任周兴江回忆,那时国内高校几乎全部上阵,还在读大四的他隔几天就能在报纸上看到相关进展,许多年轻人的研究道路就此改变。
此时的赵忠贤做出了一个决定,他和陈立泉联名向国务院建议成立国家超导实验室(现超导国家重点实验室)并获得批准,赵忠贤任首届实验室主任。
1991年,物理所超导国家重点实验室通过验收;次年,中国科大超导研究所成立。但由于铜基超导材料延展性与柔韧性受限,加之机理研究未有突破,应用前景不明朗,研究热度逐渐散去,不少学者纷纷转行。
不过,高温超导的机理研究、新材料探索从未停止。赵忠贤常和后辈强调,这是凝聚态物理最核心最前沿的问题,而且“兴趣很重要,你有瘾了,会非常愿意做它”。
2002年起,国内举办了数届国际高温超导前沿论坛,新一代研究人才在交流中集结,周兴江、丁洪、陈根富等人相继回国,加盟物理所开展超导相关研究。
2008年,颠覆信号再次出现,中国科学家的机会来了。2月18日,日本东京工业大学细野秀雄等人报告发现26K铁基超导体。此前,人们认为实现超导的要件之一是完全抗磁,铁因自带磁性而被认为是超导研究的禁区。
得知消息时,陈仙辉正在外开会,他深知临界温度若不超过39K,意义不大。当天深夜他赶回学校,立刻组织学生讨论、实验。3月25日,经反复验证,陈仙辉小组获得了常压下临界温度43K的铁基超导体,首次在国际上突破“麦克米兰极限”。
3天后,赵忠贤和物理所研究员任治安等人报告了氟掺杂镨氧铁砷化合物的临界温度为52K;4月,他们又发现压力环境下氟掺杂钐氧铁砷化合物临界温度可升至55K。
先前的积淀不止于此。物理所研究员王楠林与陈根富等人在一周内迅速制备出掺杂样品、实现超导并完成基本性质测量。他们与同事方忠合作,最先提出铁基超导母体有自旋密度波不稳定性,随后通过中子散射实验证实。
2008年底,铁基超导研究分别入选美国《科学》、美国物理学会和欧洲物理学会评选的年度重大进展,全球燃起新一轮“超导热”。
为这一天,中国科学家在这条路上走了21年。
“从0到1的创新就像盖楼,如果地基不打、前面10层楼不盖,直接盖第11层是不可能的。”周兴江感慨道。
升华:理论+实践
每次被问到成功经验,赵忠贤总爱说“运气好”。陈仙辉也说:“我很幸运,遇上了超导研究的两次热潮。”
但在一条路上坚持几十年,绝非仅凭运气。
2008年,26K铁基超导被日本科学家发现后,赵忠贤曾反省:“这个材料的结构和正常态的物理特点与我们长期以来的研究思路完全一致,但是由于我一直认为铁会对超导不利,所以错过了首次发现的机会。”他将这次机会的错失归结为没能解放思想。
无独有偶,在铁基超导研究初期,陈仙辉实验室早就注意到钡铁砷母体,但在掺钾时,烧结温度过高使钾跟石英管反应没有掺入样品而未实现超导,最后钾掺杂的钡铁砷超导体被德国科学家发现。这次经历深刻地提醒他:“科学发现只有第一,没有第二。”
“感觉只解决现象问题,理论才解决本质问题。而这些问题的解决,一点也不能离开实践。”赵忠贤曾在论文中如此写道。
“科研需要理论和实验的基础,不然真正的新现象摆在面前时,也没有准确的认知能力。”闻海虎强调,原始创新成果需要脚踏实地、深耕细作。“成果是在实践中偶然或突然发现的,凭空想象是很难出现的。”
如果说1987年的成果是一小部分人在简陋条件下苦苦求索得来的,那么2008年前后的第二波热潮则是一群人兵分多路、多点开花。
超导国家重点实验室见证了这两次热潮。实验室主任的接力棒也从赵忠贤手中一棒棒传到闻海虎、周兴江的手上。
“中国现在很多物理机理研究跟国外平齐了。”周兴江还记得,2000年左右听海外学者说起光电子能谱,内心“非常憧憬”,而2008年后,国外回来的人却说“如果不参加国内的论坛,就不知道超导方面的最新进展”。
给年轻人作报告时,赵忠贤曾说:“坚持做某一事情,有一个在长期积累基础上产生的认识上的升华。这个升华可以意会不能言传。”
| 相关新闻: |
| 赵忠贤:“土炮”搞超导,也管用 |
综合新闻